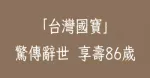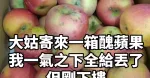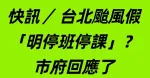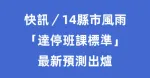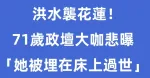3/5
下一頁
多爾袞能力有多強?沒有他,清朝都不一定能入主中原!

3/5
馬景濤版多爾袞
但光這些還是不夠的,還得安撫人心。
入關的同時,多爾袞就將大量明朝宗室、勛貴、外戚、太監的土地收為軍屯,然後交給流民和官兵屯種:
州縣衛所無主荒地准流民及官兵屯種,有主荒地則令原主墾種,無力耕種者官給牛具籽種……開荒之地三年後升科, 熟地拋荒而經墾種者一年後起科。
這些措施,相當於讓流民有了對土地的所有權,身份轉變成自耕農,自然不會被裹挾了。
在農業時代,自耕農是封建王朝統治穩定的基礎,士紳則是封建王朝基層穩壓器。自耕農有了田地得以穩定,士紳這個過程中也保證了利益,不會再像對李自成、張獻忠那樣仇視態度。
農業時代,自耕農是封建王朝統治穩定的基礎,士紳則是封建王朝基層穩壓器
既然夏稅基本收不上來,索性就不要了,多爾袞直接下令減稅,賣個好給天下人,緩解社會矛盾的同時還能重建社會秩序。
而後就是減免賦稅,當然,減稅之前,則是下令,所有的八旗子弟是不用交稅的,畢竟八旗,才是清朝統治的基本盤。
八旗免稅令:「辛丑上以中原平定免盛京滿洲漢人額輸糧草布疋。」
減稅令:「嘗聞德惟善政。政在養民。養民之道必省刑罰薄稅斂。然後風俗醇而民生遂。」
當然,這條命令除了減稅之外,還告訴天下人,清朝治理天下的綱領是省刑罰,薄稅負。
那如何省刑罰呢?多爾袞又下令,在五月二日之前的所有作姦犯科者,全部大赦,另外一些小事情,不允許入京越訴,且嚴厲打擊陷害良民的惡意訴訟。
至於薄稅負,除了此前的減稅之外,就是取消三餉和攤買。
所謂「三餉」,即明末加派的遼餉、剿餉與練餉的合稱,賦稅過重不說,一些小吏還打著徵收三餉的旗號,從中漁利。
錢收了不少,但很多卻沒到前線
而「攤買」,也就是攤派買糧,即朝廷收購民間的糧食,但明末天災人禍,糧食價格已經到了一石四五兩銀子的地步,是萬曆時期的四倍,但朝廷卻依舊按照萬曆時期的糧價強行收購,普通農民,完全沒有活路。
為此,多爾袞宣布,從順治元年(1644年)開始:「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、盡行蠲免。各該撫按、即行所屬各道府州縣軍衛衙門大張榜示。」
至於一些從稅收中漁利的貪官,直接處死,隱瞞不報或者包庇,也處死:「如有官吏朦朧混征暗派者察實糾參。必殺無赦。倘縱容不舉。即與同坐。」
說白了,就是防止士紳有組織進行抗稅,畢竟明末,士紳抗稅、拖稅、欠稅習慣了,難免在清初也是如此,通過重拳出擊,防止士紳組織起來,又嚴防朝廷官員結黨,讓地方士紳沒有了高層利益代言人,無法形成有效的利益體,從而保證稅收的穩定,也防止稅收過程中,稅賦全被轉嫁給自耕農的情況。
一套組合拳下來,清朝算是暫時獲得了民心,到了九月份,順治不僅站穩腳跟,甚至還能收了不少稅收。
到了九月份,順治不僅站穩腳跟,甚至還能收了不少稅收
根據《世祖實錄》記載,順治元年(1644年)末,朝廷一共收取了158,973兩鹽稅和71,663,900鑄錢。
一般來說,一兩銀子能兌換1000鑄錢,但實際兌換,其實是在1000-1500波動,這些收上來的錢,相當於70000兩-47000兩左右,換句話說,清朝入關第一年,收取的稅銀也就二十來萬兩。
當然,還有前明皇莊帶來的收入,雖然不多,但清朝入關僅僅一年,國庫居然有了盈餘,聽起來像天方夜譚,但的確如此。
為啥呢?自然是支出的錢少了太多了。
首先明朝的宗室祿米不需要給了,早在嘉靖四十一年(1562年)的時候,御史林潤就說過,光是河南和山西,一年祿米就需要二百三十萬石,更別說其他省份了,到了明末,數字更多,而現在,這些都省下來了。
但光這些還是不夠的,還得安撫人心。
入關的同時,多爾袞就將大量明朝宗室、勛貴、外戚、太監的土地收為軍屯,然後交給流民和官兵屯種:
州縣衛所無主荒地准流民及官兵屯種,有主荒地則令原主墾種,無力耕種者官給牛具籽種……開荒之地三年後升科, 熟地拋荒而經墾種者一年後起科。
這些措施,相當於讓流民有了對土地的所有權,身份轉變成自耕農,自然不會被裹挾了。
在農業時代,自耕農是封建王朝統治穩定的基礎,士紳則是封建王朝基層穩壓器。自耕農有了田地得以穩定,士紳這個過程中也保證了利益,不會再像對李自成、張獻忠那樣仇視態度。
農業時代,自耕農是封建王朝統治穩定的基礎,士紳則是封建王朝基層穩壓器
既然夏稅基本收不上來,索性就不要了,多爾袞直接下令減稅,賣個好給天下人,緩解社會矛盾的同時還能重建社會秩序。
而後就是減免賦稅,當然,減稅之前,則是下令,所有的八旗子弟是不用交稅的,畢竟八旗,才是清朝統治的基本盤。
八旗免稅令:「辛丑上以中原平定免盛京滿洲漢人額輸糧草布疋。」
減稅令:「嘗聞德惟善政。政在養民。養民之道必省刑罰薄稅斂。然後風俗醇而民生遂。」
當然,這條命令除了減稅之外,還告訴天下人,清朝治理天下的綱領是省刑罰,薄稅負。
那如何省刑罰呢?多爾袞又下令,在五月二日之前的所有作姦犯科者,全部大赦,另外一些小事情,不允許入京越訴,且嚴厲打擊陷害良民的惡意訴訟。
至於薄稅負,除了此前的減稅之外,就是取消三餉和攤買。
所謂「三餉」,即明末加派的遼餉、剿餉與練餉的合稱,賦稅過重不說,一些小吏還打著徵收三餉的旗號,從中漁利。
錢收了不少,但很多卻沒到前線
而「攤買」,也就是攤派買糧,即朝廷收購民間的糧食,但明末天災人禍,糧食價格已經到了一石四五兩銀子的地步,是萬曆時期的四倍,但朝廷卻依舊按照萬曆時期的糧價強行收購,普通農民,完全沒有活路。
為此,多爾袞宣布,從順治元年(1644年)開始:「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、盡行蠲免。各該撫按、即行所屬各道府州縣軍衛衙門大張榜示。」
至於一些從稅收中漁利的貪官,直接處死,隱瞞不報或者包庇,也處死:「如有官吏朦朧混征暗派者察實糾參。必殺無赦。倘縱容不舉。即與同坐。」
說白了,就是防止士紳有組織進行抗稅,畢竟明末,士紳抗稅、拖稅、欠稅習慣了,難免在清初也是如此,通過重拳出擊,防止士紳組織起來,又嚴防朝廷官員結黨,讓地方士紳沒有了高層利益代言人,無法形成有效的利益體,從而保證稅收的穩定,也防止稅收過程中,稅賦全被轉嫁給自耕農的情況。
一套組合拳下來,清朝算是暫時獲得了民心,到了九月份,順治不僅站穩腳跟,甚至還能收了不少稅收。
到了九月份,順治不僅站穩腳跟,甚至還能收了不少稅收
根據《世祖實錄》記載,順治元年(1644年)末,朝廷一共收取了158,973兩鹽稅和71,663,900鑄錢。
一般來說,一兩銀子能兌換1000鑄錢,但實際兌換,其實是在1000-1500波動,這些收上來的錢,相當於70000兩-47000兩左右,換句話說,清朝入關第一年,收取的稅銀也就二十來萬兩。
當然,還有前明皇莊帶來的收入,雖然不多,但清朝入關僅僅一年,國庫居然有了盈餘,聽起來像天方夜譚,但的確如此。
為啥呢?自然是支出的錢少了太多了。
首先明朝的宗室祿米不需要給了,早在嘉靖四十一年(1562年)的時候,御史林潤就說過,光是河南和山西,一年祿米就需要二百三十萬石,更別說其他省份了,到了明末,數字更多,而現在,這些都省下來了。
 呂純弘 • 7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1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1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5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滿素荷 • 3K次觀看
滿素荷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33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3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 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
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