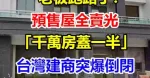3/3
下一頁
丁汝昌墓被炸焚遺體,棺木改椅凳,百年忠骨化為家具

3/3
外地遊客來此尋訪舊址,發現墓碑在,墓冢無,碑背無銘。再往村中問起,村民諱莫如深,只說「那個年頭亂,不記得了」。其實記得清楚,誰鋸的棺,誰點的火,誰用的板凳,村裡老人都知道。只是不願講,也不願聽。
曾有一所中學組織學生到此掃墓,講解員講丁汝昌生平時,避開墓被炸、骨被焚的細節,只講他如何英勇自盡。學生中有個本村孩子,悄悄說:「那凳子我奶奶坐過。」講解員臉色一變,拉他出去,再沒讓他講話。
歷史記憶就這樣被抹去了一半,留下的只是被包裝的英勇和一塊空心石碑。有心人將墓毀經過寫入村志,可上級審查時刪去,說「不利於積極正面引導」。村志成書那年,墓已修好八年,墓碑依舊乾淨如新,唯獨少了「1960年」這個數字。
丁汝昌不是唯一一位被掘墓的名臣,在那段風暴中,忠良之骨遍地成灰,歷史成了農具原料。可他的故事被記下了,被村人偷偷寫進筆記,被學生在作文中提及,被記者在專訪中寫出。丁汝昌的墓,不僅是忠臣之墓,更是那個時代荒唐記憶的墓。
村口現在立著一塊木牌:「烈士忠骨,不可侵擾。」旁邊是紀念牆,刻著「甲午忠魂」四字。沒人提起那八張凳子去哪了,也沒人說砧板是誰家用過。人們選擇性遺忘,也試圖修復,這本身就是中國鄉村對待歷史的一種複雜方式。
是忘記,還是銘記?沒人能回答。但那棺木的裂紋,那焚屍的火光,那「紅黑兩棺」的舊事,像針一樣扎在集體記憶里。忘不掉,也道不明。
歷史沉默,忠魂無聲;八條凳子撐不住烈士的冤。
曾有一所中學組織學生到此掃墓,講解員講丁汝昌生平時,避開墓被炸、骨被焚的細節,只講他如何英勇自盡。學生中有個本村孩子,悄悄說:「那凳子我奶奶坐過。」講解員臉色一變,拉他出去,再沒讓他講話。
歷史記憶就這樣被抹去了一半,留下的只是被包裝的英勇和一塊空心石碑。有心人將墓毀經過寫入村志,可上級審查時刪去,說「不利於積極正面引導」。村志成書那年,墓已修好八年,墓碑依舊乾淨如新,唯獨少了「1960年」這個數字。
丁汝昌不是唯一一位被掘墓的名臣,在那段風暴中,忠良之骨遍地成灰,歷史成了農具原料。可他的故事被記下了,被村人偷偷寫進筆記,被學生在作文中提及,被記者在專訪中寫出。丁汝昌的墓,不僅是忠臣之墓,更是那個時代荒唐記憶的墓。
村口現在立著一塊木牌:「烈士忠骨,不可侵擾。」旁邊是紀念牆,刻著「甲午忠魂」四字。沒人提起那八張凳子去哪了,也沒人說砧板是誰家用過。人們選擇性遺忘,也試圖修復,這本身就是中國鄉村對待歷史的一種複雜方式。
是忘記,還是銘記?沒人能回答。但那棺木的裂紋,那焚屍的火光,那「紅黑兩棺」的舊事,像針一樣扎在集體記憶里。忘不掉,也道不明。
歷史沉默,忠魂無聲;八條凳子撐不住烈士的冤。
 呂純弘 • 18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4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4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16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16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8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8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20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2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K次觀看 管輝若 • 8K次觀看
管輝若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40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40K次觀看 管輝若 • 7K次觀看
管輝若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4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6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6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12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1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0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