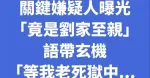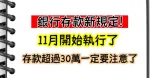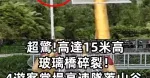3/3
下一頁
徹底躺平的陶淵明:晚年為生存乞討,5子無一成器,63歲活活餓死

3/3
要飯這事算是耗盡了最後一點精神頭。
陶淵明六十三歲那年冬天,他躺在冰冷的草蓆上,連起身討飯的氣力都沒了。
其實,陶淵明身上的病本不至於死,可飢餓和寒冷一點一點磨滅了他意志。
臨終前,陶淵明給兒子們寫了封遺書《與子儼等書》,裡頭終於說了實話:「僶俛辭世,使汝等幼而饑寒」,我死腦筋非要辭官守窮,害你們從小挨餓受凍啊!
他想起東漢隱士王霸的事:客人穿得光鮮亮麗,王霸兒子低頭看看自己破衣爛衫,羞得好幾天不說話。
王霸妻子安慰丈夫:「既然選了隱居,窮就是該付的代價,有什麼好難過?」
陶淵明提起這舊事,表面是寬慰自己,字縫裡卻全是悔意。
他悔的不只是自己受窮,更悔連累了兒女,當年要是勤快點,少灌幾口黃湯,多教孩子識文斷字,他們何至於像現在這樣,除了一把傻力氣啥都不會?
至於陶淵明的後代後來怎樣了?
他五個兒子名字在史書里再沒出現過,跟著他們父親一樣默默無聞。
可幾百年後,不少地方冒出了陶家人。
重慶豐都縣陶家坪村的人說他們是陶淵明大兒子陶儼的後代。
明朝初年搬到這裡,代代守「晴耕雨讀」的老規矩,邊種地邊辦學堂。
1937年蓋起陶氏宗祠,牆上刻著「勤學振家聲,詩書傳薪火」的祖訓。
當年族裡人陶用賓變賣家當辦「用賓中學」,窮孩子上學只收一半學費。
後來這裡還當過抗戰時期的地下黨聯絡點。到2021年,老祠堂改成「新豐書院」,書聲琅琅的傳統一直沒斷。
回頭想想陶淵明的「歸隱」,面上看是不肯同流合污,骨子裡還是對現實的逃避。
他厭惡官場烏糟事,又拗不過東晉那個僵死世道,最後躲進田園圖清凈。
可田園也沒給他安穩,喝酒誤了農事,懶散害了子女。
臨終那句「使汝等幼而饑寒」的懺悔,藏著個老父親遲來的醒悟。
他原以為遠離官場能守住骨氣,卻不知道躺平救不了命。飯碗都端不穩時,骨氣不過是空話。
倒是幾百年後,散在天南地北的那些陶姓人家,不知不覺把先人的遺憾補上了些。
當然,這些後人未必個個真是陶淵明的血脈,可卻實實在在活出了陶淵明當年想過又沒能過成的日子,心裡守著桃花源的清凈,手上該乾的活、該擔的責一點也沒落下。
陶淵明六十三歲那年冬天,他躺在冰冷的草蓆上,連起身討飯的氣力都沒了。
其實,陶淵明身上的病本不至於死,可飢餓和寒冷一點一點磨滅了他意志。
臨終前,陶淵明給兒子們寫了封遺書《與子儼等書》,裡頭終於說了實話:「僶俛辭世,使汝等幼而饑寒」,我死腦筋非要辭官守窮,害你們從小挨餓受凍啊!
他想起東漢隱士王霸的事:客人穿得光鮮亮麗,王霸兒子低頭看看自己破衣爛衫,羞得好幾天不說話。
王霸妻子安慰丈夫:「既然選了隱居,窮就是該付的代價,有什麼好難過?」
陶淵明提起這舊事,表面是寬慰自己,字縫裡卻全是悔意。
他悔的不只是自己受窮,更悔連累了兒女,當年要是勤快點,少灌幾口黃湯,多教孩子識文斷字,他們何至於像現在這樣,除了一把傻力氣啥都不會?
至於陶淵明的後代後來怎樣了?
他五個兒子名字在史書里再沒出現過,跟著他們父親一樣默默無聞。
可幾百年後,不少地方冒出了陶家人。
重慶豐都縣陶家坪村的人說他們是陶淵明大兒子陶儼的後代。
明朝初年搬到這裡,代代守「晴耕雨讀」的老規矩,邊種地邊辦學堂。
1937年蓋起陶氏宗祠,牆上刻著「勤學振家聲,詩書傳薪火」的祖訓。
當年族裡人陶用賓變賣家當辦「用賓中學」,窮孩子上學只收一半學費。
後來這裡還當過抗戰時期的地下黨聯絡點。到2021年,老祠堂改成「新豐書院」,書聲琅琅的傳統一直沒斷。
回頭想想陶淵明的「歸隱」,面上看是不肯同流合污,骨子裡還是對現實的逃避。
他厭惡官場烏糟事,又拗不過東晉那個僵死世道,最後躲進田園圖清凈。
可田園也沒給他安穩,喝酒誤了農事,懶散害了子女。
臨終那句「使汝等幼而饑寒」的懺悔,藏著個老父親遲來的醒悟。
他原以為遠離官場能守住骨氣,卻不知道躺平救不了命。飯碗都端不穩時,骨氣不過是空話。
倒是幾百年後,散在天南地北的那些陶姓人家,不知不覺把先人的遺憾補上了些。
當然,這些後人未必個個真是陶淵明的血脈,可卻實實在在活出了陶淵明當年想過又沒能過成的日子,心裡守著桃花源的清凈,手上該乾的活、該擔的責一點也沒落下。
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