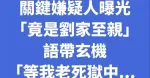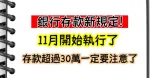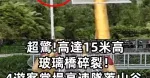1/3
下一頁
徹底躺平的陶淵明:晚年為生存乞討,5子無一成器,63歲活活餓死

1/3
徹底躺平的陶淵明:晚年為生存乞討,5子無一成器,63歲活活餓死
陶淵明四十歲扔掉彭澤縣令的官印時,外人看他瀟洒得很。
採菊東籬下,悠然見南山,多少人羨慕這樣自在的日子。
可沒人知道,這已經是他第五次辭官了。
前頭十三年里,他一直在做官和歸隱之間打轉。
每次辭官都罵官場黑暗,可過不了多久又得回去當差。
原因就一個字:窮。這個窮字像影子似的跟著他,甩也甩不掉。
陶淵明的窮是有來由的。
他一輩子娶過三房媳婦。
頭一個媳婦生孩子時難產死了,沒留下兒女。
第二個媳婦陳氏六年里給他生了四個兒子,老三老四還是雙胞胎。
這麼連著生養,陳氏身子熬垮了,早早過世。
後來又娶了第三個媳婦翟氏,比他小十二歲,又添了一兒一女。
算下來陶淵明整整六個孩子需要養活。
孩子要吃飯穿衣,頭疼腦熱得抓藥,這花銷就像無底洞。
好在母親孟老太太還在,能幫著照料。
可老人家一去世,擔子全落在陶淵明一人肩上。
那會兒他寫詩說「晨興理荒穢,帶月荷鋤歸」,天不亮下地幹活,月亮出來才回家,累得腰都直不起,可鍋里米還是不夠吃。
其實,陶淵明頭兩年歸隱生活還過得去,做官攢的錢勉強夠用。
偏偏第三年遇上火災,辛苦蓋的草屋、存的糧食、用的傢伙什,一股腦全燒光了。
陶淵明站在黑糊糊的廢墟前頭,才真真切切覺出歸隱的代價。
這些都沒什麼,更要命的是他自己不爭氣。
陶淵明愛喝酒,愛到什麼地步?下田鋤地都在腰上掛個酒壺,鋤幾下就要抿一口,喝迷糊了就往樹蔭下一躺。
他那首「種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」說得明白:豆苗沒長几棵,雜草倒長得比莊稼還高。
鄰居見了直搖頭,勸他勤快點鋤草,他倒振振有詞:「我月亮出來才收工,還不夠勤快?」
這樣幹活,地里能有好收成才怪。
寒冬臘月最是難熬。
冷風順著茅草牆縫往裡灌,米缸隔三差五就空了。
陶淵明在詩里寫實情:「夏日長抱飢,寒夜無被眠」,夏天餓肚子,冬天沒厚被子,蜷在炕上凍得直哆嗦;
「造夕思雞鳴,及晨願鳥遷」,天黑盼雞叫,天亮了又嫌日頭走得慢,饑寒交迫的滋味,每分每秒都是煎熬。
而且,受苦的不只陶淵明自己,五個孩子也跟著遭罪。
按說家裡有地,總該餓不著。可他五個兒子個個不成器。
老大阿舒十六了,天天睡到日上三竿,喊他下地比上天還難;
老二阿宣十五,看見書本就躲;
雙胞胎阿雍阿端都十三了,連六和七都分不清;
小兒子阿佟才九歲,滿腦子就想著鍋里有沒有吃的。
陶淵明還專門寫了首《責子》詩數落兒子們。寫完最後幾句,他嘆著氣說:「天運苟如此,且進杯中物」,都是命不好啊,管不了那麼多,喝酒吧!
陶淵明把錯都推到老天爺頭上,沒想過這爛攤子是自己一手造成的。
孩子們打小看著他日日醉酒,看著他幹活糊弄事,聽他說「爾之不才,亦已焉哉」,你要是不成才,那就算了唄,哪還會覺得讀書種地是正經營生?
而且,陶淵明家裡又沒人管束,三房媳婦兩個早逝,翟氏要照顧六個孩子,哪顧得上管教?
孩子們跟著學樣,把陶淵明那套懶散功夫學了個十足十。
五十歲往後,日子越過越慘。
陶淵明年輕時喝空的酒罈子,如今都化作病痛找上門來。
收成一年比一年差,家裡經常斷糧。病得起不了床時,他只能蜷在漏風的屋檐底下,寫什麼「負疴頹檐下,終日無一欣」。
最叫他寒心的是兒子們一個都指望不上。他們自己種地都糊弄,能混飽自己肚子就不錯了,哪顧得上老爹?
陶淵明四十歲扔掉彭澤縣令的官印時,外人看他瀟洒得很。
採菊東籬下,悠然見南山,多少人羨慕這樣自在的日子。
可沒人知道,這已經是他第五次辭官了。
前頭十三年里,他一直在做官和歸隱之間打轉。
每次辭官都罵官場黑暗,可過不了多久又得回去當差。
原因就一個字:窮。這個窮字像影子似的跟著他,甩也甩不掉。
陶淵明的窮是有來由的。
他一輩子娶過三房媳婦。
頭一個媳婦生孩子時難產死了,沒留下兒女。
第二個媳婦陳氏六年里給他生了四個兒子,老三老四還是雙胞胎。
這麼連著生養,陳氏身子熬垮了,早早過世。
後來又娶了第三個媳婦翟氏,比他小十二歲,又添了一兒一女。
算下來陶淵明整整六個孩子需要養活。
孩子要吃飯穿衣,頭疼腦熱得抓藥,這花銷就像無底洞。
好在母親孟老太太還在,能幫著照料。
可老人家一去世,擔子全落在陶淵明一人肩上。
那會兒他寫詩說「晨興理荒穢,帶月荷鋤歸」,天不亮下地幹活,月亮出來才回家,累得腰都直不起,可鍋里米還是不夠吃。
其實,陶淵明頭兩年歸隱生活還過得去,做官攢的錢勉強夠用。
偏偏第三年遇上火災,辛苦蓋的草屋、存的糧食、用的傢伙什,一股腦全燒光了。
陶淵明站在黑糊糊的廢墟前頭,才真真切切覺出歸隱的代價。
這些都沒什麼,更要命的是他自己不爭氣。
陶淵明愛喝酒,愛到什麼地步?下田鋤地都在腰上掛個酒壺,鋤幾下就要抿一口,喝迷糊了就往樹蔭下一躺。
他那首「種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」說得明白:豆苗沒長几棵,雜草倒長得比莊稼還高。
鄰居見了直搖頭,勸他勤快點鋤草,他倒振振有詞:「我月亮出來才收工,還不夠勤快?」
這樣幹活,地里能有好收成才怪。
寒冬臘月最是難熬。
冷風順著茅草牆縫往裡灌,米缸隔三差五就空了。
陶淵明在詩里寫實情:「夏日長抱飢,寒夜無被眠」,夏天餓肚子,冬天沒厚被子,蜷在炕上凍得直哆嗦;
「造夕思雞鳴,及晨願鳥遷」,天黑盼雞叫,天亮了又嫌日頭走得慢,饑寒交迫的滋味,每分每秒都是煎熬。
而且,受苦的不只陶淵明自己,五個孩子也跟著遭罪。
按說家裡有地,總該餓不著。可他五個兒子個個不成器。
老大阿舒十六了,天天睡到日上三竿,喊他下地比上天還難;
老二阿宣十五,看見書本就躲;
雙胞胎阿雍阿端都十三了,連六和七都分不清;
小兒子阿佟才九歲,滿腦子就想著鍋里有沒有吃的。
陶淵明還專門寫了首《責子》詩數落兒子們。寫完最後幾句,他嘆著氣說:「天運苟如此,且進杯中物」,都是命不好啊,管不了那麼多,喝酒吧!
陶淵明把錯都推到老天爺頭上,沒想過這爛攤子是自己一手造成的。
孩子們打小看著他日日醉酒,看著他幹活糊弄事,聽他說「爾之不才,亦已焉哉」,你要是不成才,那就算了唄,哪還會覺得讀書種地是正經營生?
而且,陶淵明家裡又沒人管束,三房媳婦兩個早逝,翟氏要照顧六個孩子,哪顧得上管教?
孩子們跟著學樣,把陶淵明那套懶散功夫學了個十足十。
五十歲往後,日子越過越慘。
陶淵明年輕時喝空的酒罈子,如今都化作病痛找上門來。
收成一年比一年差,家裡經常斷糧。病得起不了床時,他只能蜷在漏風的屋檐底下,寫什麼「負疴頹檐下,終日無一欣」。
最叫他寒心的是兒子們一個都指望不上。他們自己種地都糊弄,能混飽自己肚子就不錯了,哪顧得上老爹?
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