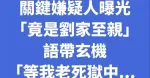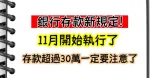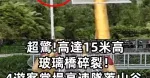3/3
下一頁
1444年,楊士奇仰屋竊嘆、哀叫數聲後身亡,朱祁鎮:匹夫誤我大事

3/3
這場鬧劇般的御駕親征從一開始就漏洞百出,糧草不繼、指揮混亂、情報錯誤。
當明軍行至土木堡時,瓦剌騎兵切斷了水源,將疲憊不堪的明軍團團圍住。
在那個血腥的下午,大明最精銳的京營全軍覆沒,隨行文武大臣五十餘人戰死,朱祁鎮本人也成了瓦剌的俘虜。
被囚禁在蒙古包里的朱祁鎮,面對也先可汗的譏諷,竟然脫口而出:
"都是楊士奇那個老匹夫誤我大事!"
這句話通過瓦剌使臣之口傳回北京,滿朝譁然。
一個已經去世七年的老臣,竟要為當朝皇帝的愚蠢決策承擔責任,這恐怕是歷史上最荒唐的甩鍋。
朱祁鎮指責楊士奇當年建議放棄開平衛,導致邊防虛弱。
但他刻意忽略了一個事實,從宣德年間到正統初年,瓦剌一直向明朝稱臣納貢,邊境並無大戰。
真正的危機,恰恰始於王振擅權後對蒙古諸部的輕慢與挑釁。
仔細審視土木堡之變的來龍去脈,不難發現這場災難的種子早已埋下。
王振為了炫耀武功,故意壓低瓦剌使團的賞賜,他挪用邊防軍費修建自家寺廟,他排擠有經驗的邊將,任用親信。
當也先可汗的大軍壓境時,又是王振朝令夕改,先是倉促決定親征,後又為保護自家糧隊臨時改道,最終將大軍帶入絕境。
這些致命的錯誤決策,沒有一個是楊士奇參與過的。
這位「大明戰神」直到臨終前,他才在遺詔中委婉承認"曩者北征非計",卻始終沒有為汙衊楊士奇道歉。
楊士奇的悲劇在於,他一生都在努力為王朝培養合格的君主,卻低估了皇權本身的腐蝕性。
當國家強盛時,他的功績被歸於聖明君主,當國家危難時,他的過失卻被無限放大。
其實站在更宏大的歷史視角看,楊士奇的遭遇不是個例。
中國歷史上類似的忠臣悲劇反覆上演,從比干到岳飛,從於謙到張居正。
這些人的共同點是他們都試圖在體制內修補漏洞,卻終被體制反噬。
他們的悲劇不在於個人才能的局限,而是始終相信可以通過勸諫明君來實現政治清明。
結局就是,這種理想主義在現實中往往碰得頭破血流。
當明軍行至土木堡時,瓦剌騎兵切斷了水源,將疲憊不堪的明軍團團圍住。
在那個血腥的下午,大明最精銳的京營全軍覆沒,隨行文武大臣五十餘人戰死,朱祁鎮本人也成了瓦剌的俘虜。
被囚禁在蒙古包里的朱祁鎮,面對也先可汗的譏諷,竟然脫口而出:
"都是楊士奇那個老匹夫誤我大事!"
這句話通過瓦剌使臣之口傳回北京,滿朝譁然。
一個已經去世七年的老臣,竟要為當朝皇帝的愚蠢決策承擔責任,這恐怕是歷史上最荒唐的甩鍋。
朱祁鎮指責楊士奇當年建議放棄開平衛,導致邊防虛弱。
但他刻意忽略了一個事實,從宣德年間到正統初年,瓦剌一直向明朝稱臣納貢,邊境並無大戰。
真正的危機,恰恰始於王振擅權後對蒙古諸部的輕慢與挑釁。
仔細審視土木堡之變的來龍去脈,不難發現這場災難的種子早已埋下。
王振為了炫耀武功,故意壓低瓦剌使團的賞賜,他挪用邊防軍費修建自家寺廟,他排擠有經驗的邊將,任用親信。
當也先可汗的大軍壓境時,又是王振朝令夕改,先是倉促決定親征,後又為保護自家糧隊臨時改道,最終將大軍帶入絕境。
這些致命的錯誤決策,沒有一個是楊士奇參與過的。
這位「大明戰神」直到臨終前,他才在遺詔中委婉承認"曩者北征非計",卻始終沒有為汙衊楊士奇道歉。
楊士奇的悲劇在於,他一生都在努力為王朝培養合格的君主,卻低估了皇權本身的腐蝕性。
當國家強盛時,他的功績被歸於聖明君主,當國家危難時,他的過失卻被無限放大。
其實站在更宏大的歷史視角看,楊士奇的遭遇不是個例。
中國歷史上類似的忠臣悲劇反覆上演,從比干到岳飛,從於謙到張居正。
這些人的共同點是他們都試圖在體制內修補漏洞,卻終被體制反噬。
他們的悲劇不在於個人才能的局限,而是始終相信可以通過勸諫明君來實現政治清明。
結局就是,這種理想主義在現實中往往碰得頭破血流。
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8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3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