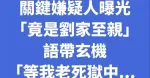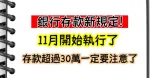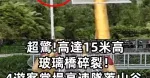4/8
下一頁
丁玲情史:「三人行」驚世駭俗,82歲臨終仍向小13歲的丈夫索吻

4/8
1928年,丁玲僅僅用了14天時間,就完成了兩萬六千字的《莎菲女士的日記》。
丁玲筆下的莎菲女士死了朋友,找不到跟自己有共同語言的人,非常孤獨。
她是一個出走的「娜拉」,有一點錢,不需要靠男人。
她游離在兩個男人之間,最終卻誰也不選擇,獨自前行——
葦弟非常喜歡莎菲,對莎菲非常好,但是沒有莎菲聰明、堅強;
莎菲對凌吉士一見傾心,但是他對莎菲並不是真心,所以莎菲把他也拋棄了。
這部作品讓丁玲一夜成名,「好似在這死寂的文壇上,拋下一顆炸彈一樣,大家都不免為她的天才所震驚了」,也帶來了豐厚的稿酬。
但是,這也讓胡也頻愈發顯得像小說里的「葦弟」,女強男弱更加明顯。
就在這段感情岌岌可危之際,丁玲的「凌吉士」——馮雪峰出現了。
04
丁玲有了錢,萌生了去日本留學的念頭。
於是,朋友介紹馮雪峰,來教丁玲學日文。
出乎意料的是,師生關係僅維持了一天,兩人便暢懷地談起國事,談起文學,然後談起了戀愛。
馮雪峰,共產黨人,1903年出生在浙江義烏一個農民家庭。
他本是杭州西湖邊的「湖畔詩人」,他的詩作《小詩》中寫道:
「我愛小孩子,小狗,小鳥,小樹,小草,所以我也愛做小詩。」
這位詩人也在迫切地尋求生命的知己,他的另一首詩《拾首春的歌》中有這樣的句子:
「沒有一株楊柳不為李花而癲狂,沒有一水不為東風吹皺,沒有一個戀人,不為戀人惱著。」
於是,當兩個寂寞的文學青年相遇,他們立馬有了一見鍾情、相逢恨晚之感。
丁玲後來回憶道:
「一見鍾情就是許多男女具有的一種特別的『靈感』,也可稱為『精神的閃光』,但不是『衝動』之類的東西。他之所以吸引你,那是因為你的愛好、喜歡的東西,早就儲存在那裡,所以,一旦在人群中發現他,便會引起一種我不叫『衝動』,就叫『靈感』吧。」
然而,此時的胡也頻依然深愛著丁玲,他的愛純粹得不求回報:
「我也不要你愛我, 只要允許我對你好就行了。」
面對這樣赤誠的感情,丁玲陷入了兩難。
最終,她大膽地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解決方案:
「為什麼我們不能三個人一起生活呢?」
這個提議,將在西湖邊掀起一場情感風暴。
05
1928年2月,三人一起前往杭州生活。
馮雪峰在西湖邊租了一個獨立的院子,院子有兩個臥室。
兩個男人各一個房間,丁玲每天輪流在兩個房間過夜。
一周後,胡也頻受不了了,他跑到上海跟好友沈從文哭訴:
「我已準備不再迴轉杭州!」
沈從文教胡也頻又爭又搶:
「你真是個傻瓜。你怎麼是這麼一個蠢人呢?你一定要回去,你一定要占有這個女人,你才牢靠的了,你現在這樣不就是空了嗎?」
這番話點燃了胡也頻的鬥志,他連夜趕回杭州。
丁玲後來回憶說:
「也頻走後,我和馮雪峰兩個人晚間聊了一會天,完了我就給胡也頻寫了很長一封信,寫到很晚。我們兩個人又聊了一會天,天就亮了。我們坐在走廊上聊天的時候,搞了一點什麼東西馬馬虎虎吃了,也頻就回來了。他後來告訴我,他回來看見我床上的被子、任何東西都是他走的時候一個樣子,所以非常相信我的話,他說如果要不是的話,他就要把我殺了,就不是打我了!」
丁玲從憤怒的胡也頻身上明顯感受到那種「可怕的男性的熱愛」,更何況,胡也頻時刻準備殉情。
而這種足以震懾丁玲靈魂的熱情和勇氣,恰是馮雪峰所缺乏的。
因此,在必須「二選一」的時候,丁玲最終選擇了胡也頻。
1928年7月,馮雪峰負著心靈重創,回到故鄉義烏教書。
一年後,他與小自己7歲的學生何愛玉結婚,兩人共同生活了47年。
丁玲筆下的莎菲女士死了朋友,找不到跟自己有共同語言的人,非常孤獨。
她是一個出走的「娜拉」,有一點錢,不需要靠男人。
她游離在兩個男人之間,最終卻誰也不選擇,獨自前行——
葦弟非常喜歡莎菲,對莎菲非常好,但是沒有莎菲聰明、堅強;
莎菲對凌吉士一見傾心,但是他對莎菲並不是真心,所以莎菲把他也拋棄了。
這部作品讓丁玲一夜成名,「好似在這死寂的文壇上,拋下一顆炸彈一樣,大家都不免為她的天才所震驚了」,也帶來了豐厚的稿酬。
但是,這也讓胡也頻愈發顯得像小說里的「葦弟」,女強男弱更加明顯。
就在這段感情岌岌可危之際,丁玲的「凌吉士」——馮雪峰出現了。
04
丁玲有了錢,萌生了去日本留學的念頭。
於是,朋友介紹馮雪峰,來教丁玲學日文。
出乎意料的是,師生關係僅維持了一天,兩人便暢懷地談起國事,談起文學,然後談起了戀愛。
馮雪峰,共產黨人,1903年出生在浙江義烏一個農民家庭。
他本是杭州西湖邊的「湖畔詩人」,他的詩作《小詩》中寫道:
「我愛小孩子,小狗,小鳥,小樹,小草,所以我也愛做小詩。」
這位詩人也在迫切地尋求生命的知己,他的另一首詩《拾首春的歌》中有這樣的句子:
「沒有一株楊柳不為李花而癲狂,沒有一水不為東風吹皺,沒有一個戀人,不為戀人惱著。」
於是,當兩個寂寞的文學青年相遇,他們立馬有了一見鍾情、相逢恨晚之感。
丁玲後來回憶道:
「一見鍾情就是許多男女具有的一種特別的『靈感』,也可稱為『精神的閃光』,但不是『衝動』之類的東西。他之所以吸引你,那是因為你的愛好、喜歡的東西,早就儲存在那裡,所以,一旦在人群中發現他,便會引起一種我不叫『衝動』,就叫『靈感』吧。」
然而,此時的胡也頻依然深愛著丁玲,他的愛純粹得不求回報:
「我也不要你愛我, 只要允許我對你好就行了。」
面對這樣赤誠的感情,丁玲陷入了兩難。
最終,她大膽地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解決方案:
「為什麼我們不能三個人一起生活呢?」
這個提議,將在西湖邊掀起一場情感風暴。
05
1928年2月,三人一起前往杭州生活。
馮雪峰在西湖邊租了一個獨立的院子,院子有兩個臥室。
兩個男人各一個房間,丁玲每天輪流在兩個房間過夜。
一周後,胡也頻受不了了,他跑到上海跟好友沈從文哭訴:
「我已準備不再迴轉杭州!」
沈從文教胡也頻又爭又搶:
「你真是個傻瓜。你怎麼是這麼一個蠢人呢?你一定要回去,你一定要占有這個女人,你才牢靠的了,你現在這樣不就是空了嗎?」
這番話點燃了胡也頻的鬥志,他連夜趕回杭州。
丁玲後來回憶說:
「也頻走後,我和馮雪峰兩個人晚間聊了一會天,完了我就給胡也頻寫了很長一封信,寫到很晚。我們兩個人又聊了一會天,天就亮了。我們坐在走廊上聊天的時候,搞了一點什麼東西馬馬虎虎吃了,也頻就回來了。他後來告訴我,他回來看見我床上的被子、任何東西都是他走的時候一個樣子,所以非常相信我的話,他說如果要不是的話,他就要把我殺了,就不是打我了!」
丁玲從憤怒的胡也頻身上明顯感受到那種「可怕的男性的熱愛」,更何況,胡也頻時刻準備殉情。
而這種足以震懾丁玲靈魂的熱情和勇氣,恰是馮雪峰所缺乏的。
因此,在必須「二選一」的時候,丁玲最終選擇了胡也頻。
1928年7月,馮雪峰負著心靈重創,回到故鄉義烏教書。
一年後,他與小自己7歲的學生何愛玉結婚,兩人共同生活了47年。
 呂純弘 • 1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7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7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5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4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4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7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2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2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