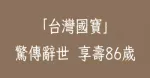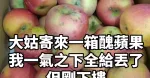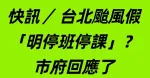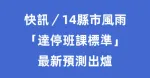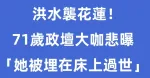3/3
下一頁
生前罵名遍天下,死後卻成民族之光,他的名字如今已鮮為人知

3/3
馬相伯的回答坦蕩而純粹:我的目的不是為了某個學校,而是為了國家培養人才,只要是為中國辦教育,我都支持。
他的一生,似乎都在失去。
早年失去信仰,中年投身政治卻失去聲譽,晚年遭遇家庭悲劇,妻子和兒子因海難喪生,母親也帶著對他的誤解離世。
他創辦了震旦,又失去了震旦。
他將萬貫家財散盡,自己成了一個「無家、無妻、無子」的「三無老人」。
但他又似乎什麼都得到了,他點燃的教育火炬,照亮了一代又一代的精英,為風雨飄搖的中國,儲備了最寶貴的人才火種。
當他再次涉足政治,無論是投票選舉孫中山,還是後來痛斥袁世凱稱帝,他始終保持著一個讀書人的風骨和底線。
他不站任何派系,只「站中國這邊」。
1931年,「九一八事變」爆發,國難當頭。
已經92歲高齡的馬相伯,再次挺身而出。
他發表《為日禍告國人書》,在4個月內發表了12次廣播演說,用自己蒼老但有力的聲音,喚醒民眾的抗日熱情。
他開始賣字籌款,一副對聯50塊,一個「壽」字30塊,所得10萬元巨款,一分不留,全部捐給前線。
1932年,他甚至當著巡邏日軍的面,在上海土山灣大書「還我河山」四字,其風骨與勇氣,令無數後輩汗顏。
當「七君子」因救國入獄,96歲的馬相伯四處奔走營救,甚至寫信給馮玉祥,表示願以「首領」身份和自己的頭顱為他們擔保。
這份擔當,徹底洗刷了半生前被強加的「漢奸」污名。
沈鈞儒等七君子獲釋後,專程拜望馬相伯,合影留念,並題字:「惟公馬首是瞻」。
1939年,馬相伯在越南諒山的流亡途中,迎來了百歲壽辰。
國民政府稱他為「國家之英,民族之瑞」,中共中央的賀電則讚譽他為「國家之光,人類之瑞」。
曾經被罵作「漢奸」的人,此刻終於得到了整個民族的最高敬意。
然而,幾個月後,這位百歲老人就在諒山的一個山洞中與世長辭。
臨終前,他留下了那句著名的悲鳴:「我是一條狗,只會叫,叫了一百年,還沒有把中國叫醒。」
這句話里,沒有功成名就的欣慰,只有對國家命運最深沉的憂慮和未竟其功的無盡悲愴。
1952年,馬相伯的靈柩被運回上海,安葬於萬國公墓。
他的墓碑上沒有羅列任何頭銜和功績,只刻著一句話:「馬相伯,復旦大學創始人」。
這或許是對他一生最好的概括。
他所有的努力,所有的毀家紓難,所有的忍辱負重,最終都凝聚成了一所大學,凝聚成了那句「日月光華,旦復旦兮」的期盼。
參考資料:
《馬相伯傳》
《復旦大學校史稿》
他的一生,似乎都在失去。
早年失去信仰,中年投身政治卻失去聲譽,晚年遭遇家庭悲劇,妻子和兒子因海難喪生,母親也帶著對他的誤解離世。
他創辦了震旦,又失去了震旦。
他將萬貫家財散盡,自己成了一個「無家、無妻、無子」的「三無老人」。
但他又似乎什麼都得到了,他點燃的教育火炬,照亮了一代又一代的精英,為風雨飄搖的中國,儲備了最寶貴的人才火種。
當他再次涉足政治,無論是投票選舉孫中山,還是後來痛斥袁世凱稱帝,他始終保持著一個讀書人的風骨和底線。
他不站任何派系,只「站中國這邊」。
1931年,「九一八事變」爆發,國難當頭。
已經92歲高齡的馬相伯,再次挺身而出。
他發表《為日禍告國人書》,在4個月內發表了12次廣播演說,用自己蒼老但有力的聲音,喚醒民眾的抗日熱情。
他開始賣字籌款,一副對聯50塊,一個「壽」字30塊,所得10萬元巨款,一分不留,全部捐給前線。
1932年,他甚至當著巡邏日軍的面,在上海土山灣大書「還我河山」四字,其風骨與勇氣,令無數後輩汗顏。
當「七君子」因救國入獄,96歲的馬相伯四處奔走營救,甚至寫信給馮玉祥,表示願以「首領」身份和自己的頭顱為他們擔保。
這份擔當,徹底洗刷了半生前被強加的「漢奸」污名。
沈鈞儒等七君子獲釋後,專程拜望馬相伯,合影留念,並題字:「惟公馬首是瞻」。
1939年,馬相伯在越南諒山的流亡途中,迎來了百歲壽辰。
國民政府稱他為「國家之英,民族之瑞」,中共中央的賀電則讚譽他為「國家之光,人類之瑞」。
曾經被罵作「漢奸」的人,此刻終於得到了整個民族的最高敬意。
然而,幾個月後,這位百歲老人就在諒山的一個山洞中與世長辭。
臨終前,他留下了那句著名的悲鳴:「我是一條狗,只會叫,叫了一百年,還沒有把中國叫醒。」
這句話里,沒有功成名就的欣慰,只有對國家命運最深沉的憂慮和未竟其功的無盡悲愴。
1952年,馬相伯的靈柩被運回上海,安葬於萬國公墓。
他的墓碑上沒有羅列任何頭銜和功績,只刻著一句話:「馬相伯,復旦大學創始人」。
這或許是對他一生最好的概括。
他所有的努力,所有的毀家紓難,所有的忍辱負重,最終都凝聚成了一所大學,凝聚成了那句「日月光華,旦復旦兮」的期盼。
參考資料:
《馬相伯傳》
《復旦大學校史稿》
 呂純弘 • 13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30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1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9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1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10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9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9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9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7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
滿素荷 • 4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3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8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5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2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9K次觀看 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
幸山輪 • 22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4K次觀看